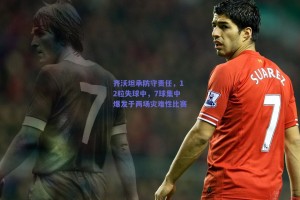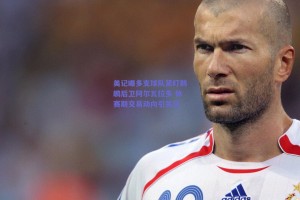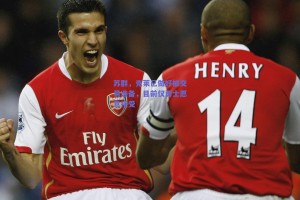王勤伯,为什么我不和日本足球共情—一场关于足球、文化与身份认同的思辨
在亚洲足坛,日本足球的崛起常被视为一个“奇迹”,从1990年代的职业化改革,到如今大批球员登陆欧洲顶级联赛,日本队已成为世界杯淘汰赛的常客,其传控打法、青训体系乃至球迷文化均被广泛推崇,在这片赞誉声中,资深体育媒体人王勤伯近期公开发表的观点却显得格外冷静甚至疏离,他直言:“我无法与日本足球共情。”这一表态迅速引发热议,不仅触及足球领域的技战术讨论,更揭开了一场关于文化认同、历史记忆与体育精神本质的深层思辨。
日本足球的“成功叙事”与共情逻辑
日本足球的成就确实令人瞩目,通过数十年的系统性建设,J联赛的成立、校园足球的普及以及“足球王国”计划的推进,日本构建了完整的金字塔体系,从三浦知良到久保建英,一代代球员的成长轨迹印证了其青训的成功,日本队在世界杯上击败德国、西班牙等强队的表现,以及球迷赛后自觉清理看台的行为,常被贴上“谦逊、坚韧、文明”的标签,这种叙事容易引发邻国的共情,尤其是那些同样渴望通过体育实现国家形象提升的亚洲地区。
共情的逻辑往往建立在两种基础上:一是对“弱者逆袭”的欣赏,二是对“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的认同,许多中国球迷对日本足球的情感投射,正是源于对本国足球长期滞后的焦虑感——日本模式似乎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王勤伯的反思恰恰挑战了这种单向度的共情,他指出,足球不仅是竞技,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而认同的边界往往由历史、政治与集体记忆塑造。

疏离感的根源:历史负重与身份自觉
王勤伯在论述中并未否定日本足球的专业成就,但他强调,共情需要情感共鸣的基础,而这一基础可能因历史语境而断裂,他以东亚近代史为例,指出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始终笼罩在殖民与战争的阴影下,尽管体育常被赋予“超越政治”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现实中,国家代表队的对抗难免唤起历史记忆,日本队球衣上的旭日旗元素、部分极右球迷的言论,均可能触发邻国民众的负面联想。

更重要的是,王勤伯认为,过度强调对日本足球的共情,可能模糊本土足球发展的主体性。“当我们一味将日本足球视为模板时,是否忽略了本国社会文化土壤的差异性?”他举例称,日本足球的成功得益于其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结构、严谨的标准化训练,但这些模式未必适用于强调个人灵活性的东南亚或南亚地区,盲目共情可能导致“削足适履”,甚至掩盖本国足球改革中的真问题——例如腐败、青训断层或急功近利。
足球世界的“共情悖论”:普世价值与民族主义
王勤伯的观点触及了一个更广泛的悖论:足球既是全球化的产物,又是民族主义的舞台,国际足联常宣扬“足球连接世界”的理念,但世界杯的国歌、国旗与国籍规则无不强化着民族边界,这种张力在亚洲尤为明显,日本足球的国际化(如归化球员、外教执教)本可成为区域合作的范例,但现实中,历史积怨与领土争端常使体育交流复杂化。
共情的局限性也体现在竞技层面,足球的本质是竞争而非和谐,对手之间天然存在对抗性,王勤伯调侃道:“若因欣赏传控足球就与日本队共情,那是否也该与德国、西班牙共情?球迷的情感归属将陷入混乱。”他认为,健康的体育文化应允许“理性的欣赏”与“有距离的观察”,而非强迫情感绑定,中国球迷可以研究日本青训细节,但无需在中日对决时为对手欢呼——这并非狭隘,而是对体育竞争本质的尊重。
超越共情:构建本土足球的文化自信
王勤伯的批判最终指向一种建设性路径:摆脱对“他者”的盲目追随,回归本土足球的文化根脉,他举例称,泰国足球的“寺院长传”传统、伊朗的街头足球活力,均展现出不同于日本模式的独特价值,中国足球也曾有“小快灵”风格,但近年因过度迷信外教或归化而迷失自我。“共情不应等同于自我否定,”他强调,“真正的进步源于对自身问题的直面,而非将他者的成功作为情感避难所。”
这种观点与全球体育学界的研究不谋而合,英国学者约瑟夫·马奎尔在《足球与全球化》中指出,后发国家常陷入“模仿陷阱”,误将西方(或日本)的体育体系视为唯一标准,反而压抑了本土创新,王勤伯认为,亚洲足球的未来在于多元共生的生态:日本可坚持其传控哲学,韩国延续体能优势,东南亚发展技术流——而中国足球需找到与自身社会文化契合的道路。
足球与情感政治的未来
王勤伯的“不共情”论,绝非对日本足球的敌意否定,而是一场关于体育与情感政治关系的清醒对话,在社交媒体时代,体育事件极易被简化为二元对立(如“精日”与“狭隘民族主义”的标签大战),但他的论述试图超越这种浅层冲突,引导公众思考:我们如何在欣赏对手的同时保持自我?如何将历史记忆转化为建设性动力?
或许,真正的体育精神既不是盲目的共情,也不是偏执的排斥,而是一种“批判性欣赏”——承认日本足球的成就,但拒绝将其神化;直面历史的重负,但不让其绑架未来,当亚洲足球能够平视彼此的成功与失败时,共情与否将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命题,而成为一种自由选择,而这,正是王勤伯留给公众的最大启示。